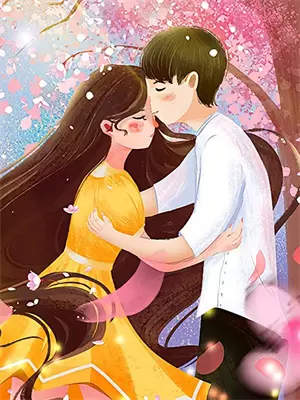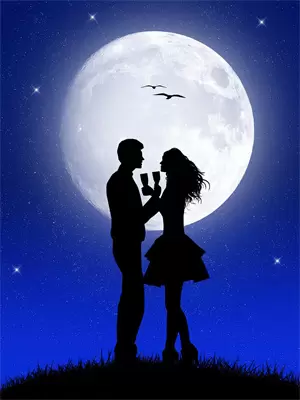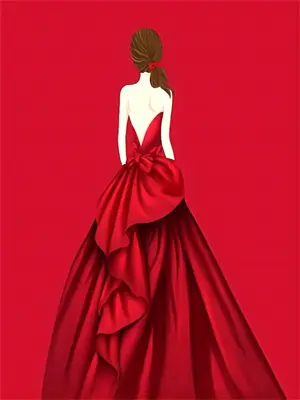
我曾以为,冷待那个身有残疾的太子,是对皇权的维护。直到他跪在殿下,用最疏离的礼仪,
泣血高呼“请陛下称太子”,我才惊觉已将他逼至绝境。后来,叛军攻入皇宫,
那个我以为怯懦无能的儿子,却拖着跛足,以身为我挡下致命一击。他倒在我怀里,
气息微弱地问:“父皇……现在,儿臣……不丢您的脸了吧?”1我是大周的皇帝,李泓。
今天是我的万寿节,普天同庆,四海来朝。我高坐于龙椅之上,
接受着万邦的朝贺与臣民的跪拜,目光所及,皆是锦绣江山,歌舞升平。我的几个儿子,
英武的、聪慧的、甚至尚在总角的幼子,都侍立在侧,他们是我血脉的延续,
是我皇权的彰显。可我的目光,总是不由自主地,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厌烦,
落向那个角落里的身影——我的太子,李昭。他安静地坐在那里,身形清瘦,面色苍白。
若非那一身明黄的太子冠服,他几乎要被淹没在勋贵皇亲的璀璨光华里。
他与他的兄弟们不同,他走动时,左腿会显出一种令人刺眼的迟滞与不稳。那道残疾,
如同我完美玉璧上的一道瑕疵,时时刻刻提醒着我,我的继承人,是个跛子。这份厌烦,
自我册立他为太子的那天起,便如影随形。他是元后嫡子,是宗法礼制下无可争议的储君。
可我每次看到他,看到的不是未来帝国的希望,而是我身为帝王的污点。一个跛脚的太子,
传出去,岂不让天下人耻笑我李氏皇族?丝竹之声愈发靡丽,舞姬的水袖扬起又落下,
如梦似幻。终于,轮到皇子们献寿礼了。二皇子献上的是一柄削铁如泥的宝剑,
三皇子呈上的是一幅前朝大家的《江山万里图》,就连年仅八岁的幼子,
也奶声奶气地献上了一尊他亲手捏的、歪歪扭扭的陶土寿星。我一一含笑嘉许,
目光扫过他们,心中是满意的。他们健康,强壮,充满了活力,
这才是我李泓的儿子该有的模样。最后,轮到了李昭。他站起身,端着一杯酒,
从他的席位上,一步,一步,艰难地向我走来。距离不远,他却走得极慢,
每一步都像在与自己的身体搏斗。大殿内的喧嚣仿佛瞬间静止,无数道目光,或同情,
或讥诮,或幸灾乐祸,全都聚焦在他那条不甚便利的腿上。我端坐着,面无表情,
心中却涌起一股难以遏制的烦躁。他为何要如此固执?为何不让内侍代劳?他难道不知,
他这副模样,走在这金碧辉煌的大殿中央,是何等的……丢人现眼。他终于走到御前,
双手举起酒杯,缓缓跪下。他的动作很稳,没有一丝颤抖,只是那跪下的过程,因为腿疾,
显得格外吃力。“儿臣,恭祝父皇福寿与天齐,圣躬万安。”他的声音清朗,
却透着一股与他年龄不符的沉寂。我没有动,甚至没有看他。我转过头,
对身边的淑妃笑道:“澈儿幼子方才捏的寿星,倒是颇有几分神韵,赏。
”我的声音不大,却足以让整个大殿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我故意忽略了他,
像忽略一件无足轻重的摆设。我就是要让他知道,在我心中,
他甚至不如一个八岁孩童歪歪扭扭的陶作。李昭高举酒杯的身影僵住了。大殿内,
死一般的寂静。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,看着这位被父皇当众羞辱的太子。
我能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的屈辱,那屈辱像冰冷的雾气,几乎要凝结成霜。
我以为他会默默退下,像过去无数次一样,将所有的难堪与不甘吞进肚里。然而,他没有。
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然后,将额头重重地叩在冰冷的金砖地面上。那一声闷响,
让我的心脏都跟着缩了一下。他没有起身,依旧保持着跪伏的姿态,声音却陡然拔高,
带着一丝破碎的颤音,响彻整个太和殿:“请陛下,称太子!”这句话,不卑不亢,
没有质问,没有怨怼,只是一句最合乎礼法的请求。他没有自称“儿臣”,
而是以储君的身份,请求我这个皇帝,在正式的场合,给予他应有的称谓。这五个字,
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,狠狠地抽在我的脸上。我的血一下子冲上了头顶。逆子!
他这是在做什么?在我的万寿节上,当着满朝文武和外邦使臣的面,指责我这个皇帝,
没有遵守君臣之礼吗?他是在用祖宗的法度,来压我这个天子吗?我心中的那点烦躁,
瞬间被滔天的怒火所取代。皇权的尊严,不容许任何形式的挑战,哪怕是来自我的儿子,
我的太子!“放肆!”我抓起案几上的鎏金酒杯,毫不犹豫地向他砸了过去。
酒杯裹挟着我的雷霆之怒,精准地砸在他的额角。他闷哼一声,身体晃了晃,却没有倒下,
依旧倔强地跪在那里。一缕鲜红的血,顺着他光洁的额角,蜿蜒滑落,滴在他面前的金砖上,
绽开一朵刺目的血花。“你这逆子!”我的声音冰冷如刀,“你是在指责朕吗?!
”他没有回答,只是将额头再次叩下,声音里已经带上了无法掩饰的泣音,
却依旧执着地重复着那句话:“请陛下……称太子。”那一刻,
我看着他伏在地上的瘦削背影,看着那蜿蜒的血迹,心中没有一丝怜悯,
只有被冒犯的、属于帝王的无边怒火。我以为我在维护皇权的尊严,却不知道,那一声闷响,
那一道血痕,正是我亲手在我们父子之间,劈开的第一道万丈深渊。2寿宴不欢而散。
我以“太子失仪,需静心思过”为由,将李昭禁足于东宫,没有我的旨意,不得踏出半步。
回到甘露殿,我余怒未消。殿内燃着上好的龙涎香,那宁神静气的味道,
此刻却让我更加心烦意乱。我挥退了所有宫人,独自在殿内踱步。那个逆子!他眼中的倔强,
他话语里的坚持,像一根根尖锐的刺,扎在我的心头。他是在挑战我,
赤裸裸地挑战我身为父亲和皇帝的双重权威。他以为凭着元后的嫡子身份,凭着祖宗的规矩,
就能让我低头吗?我冷笑一声。天真。我是皇帝,是天子。我的意志,
就是这天底下最高的规矩。他必须学会的,不是引经据典地与我对抗,而是无条件的顺从。
我走到窗边,看着东宫的方向。那里一片漆黑,沉寂得像一座坟墓。我的心中没有半分不忍,
只觉得这是他咎由自取。我需要冷一冷他,让他那颗被书本教坏了的、不知天高地厚的脑袋,
好好清醒清醒。让他明白,君就是君,父就是父,他一日是太子,便一日是我的臣子。
可不知为何,脑海中却不受控制地闪过一些久远的画面。那时的李昭,还叫恒儿。他才五岁,
还没有遭遇那场该死的意外,是个粉雕玉琢、聪慧伶俐的孩童。他会迈着小短腿,
摇摇晃晃地扑进我怀里,奶声奶气地喊我“父皇”。他会献宝似的把刚学会的字拿给我看,
满眼都是孺慕与崇拜。那时的我,也曾将他高高举过头顶,许诺他整个天下。画面一转,
又变成了他的母后,我的元后,在病榻上弥留的场景。她紧紧抓着我的手,气若游丝,
眼中满是哀求与不舍。
待我们的恒儿……他已经……已经够苦了……”“恒儿……”我下意识地低声念出这个名字,
心脏猛地一抽,泛起一丝尖锐的痛。那场意外,他为了从失控的惊马蹄下救出贪玩的二皇子,
被撞断了腿。从此,那个活泼爱笑的恒儿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,
是这个沉默寡言、步履蹒跚的李昭。我内心深处,那被帝王威严层层包裹的地方,
似乎有了一丝微不可察的松动。或许,我今天做得太过了?他毕竟是我的儿子,
毕竟是为了救他的兄弟才落下的残疾……不!这个念头刚一升起,就被我狠狠地掐灭。
我是皇帝!帝王不能有弱点,更不能有私情。“帝王心术”,
首先要磨灭的就是不必要的情感。同情、愧疚,这些都是帝王之路上的绊脚石。李昭是太子,
他未来要继承的是整个江山,区区一点委屈和羞辱都承受不住,
将来如何面对朝堂的风云诡谲,如何驾驭满朝的虎狼之臣?我这是在磨砺他,是在为他好。
对,就是这样。我深吸一口气,将那些扰乱心神的画面尽数驱散。我重新坐回龙椅,
心中的那丝松动,再次被坚冰封冻。我告诉自己,冷落他,打压他,是为了让他成长。
让他明白,只有绝对的权力,才能带来绝对的尊严。而此时,我不知道的东宫之内,
清冷得如同冰窖。李昭遣退了所有内侍,独自一人来到供奉着元后画像的内殿。他没有点灯,
只借着窗外透进的惨淡月光,看着画像上那个温柔慈爱的女子。
他额上的伤口已经简单包扎过,但血迹依旧浸透了纱布,显得触目惊心。他缓缓地,
用那条完好的腿支撐着身体,艰难地跪了下去。然后,他对着母亲的画像,
重重地磕了一个头。空寂的殿宇内,只有他压抑的、如同受伤幼兽般的呜咽。他没有哭出声,
只是无声地流着泪,泪水混着血水,从他苍白的脸上滑落,滴在冰冷的地面上。
“母后……”他绝望地低语,声音轻得像一阵风。“儿臣……让您失望了。”他以为,
只要他足够隐忍,足够顺从,就能换来父皇哪怕一丝的温情。他以为,
只要他做好一个完美的储君,就能让父皇忘掉他腿上的残疾。可他错了。在父皇眼中,
他不是儿子,不是储君,只是一个碍眼的、残缺的污点。那句“请陛下称太子”,
是他鼓起一生勇气的抗争,也是他对自己身为太子最后尊严的维护。然而,换来的,
却是更彻底的羞辱和厌弃。他伏在地上,瘦削的肩膀剧烈地颤抖着。月光照在他身上,
投下一道孤独而破碎的影子。在那一刻,他心中有什么东西,随着那滴落的血泪,
一同碎裂了。3禁足李昭的日子里,朝堂之上风平浪静,但我知道,这只是表象。
平静的水面下,暗流早已开始涌动。一份八百里加急的密报被呈到我的御案上。北境的藩王,
我的亲弟弟,燕王李慎,近期频繁调动兵马,与边境外的部族往来密切。
我看着密报上那些触目惊心的字眼,眉头微蹙。燕王一向有野心,这我不是不知道。
但北境有我布下的重兵,他想造反,无异于以卵击石。相比于这远在天边的威胁,
我更在意的,是近在咫尺的“心腹大患”。我将密报随手放到一边,转而拿起了另一份奏折。
那是我授意中书省拟定的,关于削减东宫属官及用度的新章程。“陛下,
东宫用度一向遵循祖制,如今骤然削减大半,恐引朝野议论,亦有损储君体面。
”一位老臣站出来,颤巍巍地劝谏。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:“太子闭门思过,
要那么多属官何用?至于体面,是自己挣的,不是靠排场撑的。朕看,
太子就是平日里过得太安逸了,才会在寿宴上说出那等狂悖之言。此事不必再议,
就这么定了。”我的话一锤定音,朝堂上再无人敢反对。
这是我释放出的明确信号:太子已经失了圣心。那些惯会见风使舵的墙头草,立刻心领神会。
很快,东宫门前变得门可罗雀。以往那些巴结奉承的官员,如今都绕道而行,
唯恐沾上一点晦气。一日午后,我处理完政务,在御花园中散步,
正巧碰见淑妃带着我的幼子李澈玩耍。不远处,一个身影正扶着宫墙,缓慢地挪动。是李昭。
禁足令只说不许出东宫,他倒是在自己的宫院里“活动”。李澈看见他,立刻跑了过去,
仰着天真的脸,大声问道:“太子哥哥,你的腿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呀?母妃说,你是跛子,
当不了皇帝的。”童言无忌,却最是伤人。我看见李昭的身体僵了一下。他低下头,
看着自己的弟弟,眼神里没有愤怒,也没有悲伤,只有一片死寂的平静。他没有回答,
只是沉默地、继续一步一步往前走。淑妃款款走来,假意斥责了李澈几句,
然后柔柔地靠在我身边,意有所指地吹着耳边风:“陛下,您瞧,太子殿下对您,
似乎怨念颇深啊……臣妾看他整日阴沉着脸,一句话不说,真是让人担心。
”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,李昭的背影在夕阳下被拉得很长,显得愈发孤寂。
他那份超乎寻常的平静,在我看来,就是一种无声的对抗。淑妃的话,恰好说中了我的心事。
一个心怀怨恨的太子,比一个愚蠢的太子更可怕。我的眼神,瞬间冷了下去。
我以为他会就此消沉,或者不甘心地闹出些动静来。可他什么都没做,
东宫安静得像一潭死水。这让我愈发不安。我不知道的是,就在那个夜晚,
当整个皇宫都沉入睡梦时,东宫的书房里,还亮着一豆孤灯。李昭坐在案前,
他面前跪着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仆役,那是他身边唯一一个从元后时期就跟着他的老人,
名叫福安。“都安排好了吗?”李昭的声音很低,却异常清晰。“回殿下,都已照您的吩咐,
安排妥当了。”福安沉声回答,眼中闪烁着忠诚的光芒。李昭点了点头,
目光投向窗外的黑暗,那双总是死寂的眸子里,第一次掠过一丝锐利如刀锋的光芒。
他从怀中取出一封早已写好的信,递给福安。“照计划行事。”他低语道,
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,“记住,无论发生什么,保全自己为上。
”福安重重磕了一个头,接过那封信,悄无声息地退入黑暗之中。灯火摇曳,
映着李昭苍白而坚毅的侧脸。他不是在消沉,也不是在认命。他在我看不见的地方,
用我无法想象的方式,织着一张网。这张网,不是为了他自己,而是为了我,
为了这个他依旧想要守护的、父亲的江山。而我,这个自以为是的皇帝,正一步步,
亲手将他唯一的忠诚与守护,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。4削减东宫用度的旨意下去没几天,
朝堂上便有了新的动向。御史大夫张承安,一个揣测圣意的好手,第一个站了出来,
上了一道洋洋洒洒的奏疏。核心内容只有一个:请求废黜太子李昭,另立贤明。
奏疏里列举了李昭的数条“罪状”:其一,身为储君,身有残疾,有损国体;其二,
德行有亏,于万寿节顶撞君父,大为不孝;其三,性情阴郁,不堪为未来之君主。每一条,
都正中我的下怀。我拿着那份奏折,坐在龙椅上,久久不语。满朝文武鸦雀无声,
都在等待我的决断。废太子,这是动摇国本的大事。但我知道,只要我点一下头,
这件事就会立刻成为定局。我一手造成的舆论,已经将他推到了悬崖边上。
我看着下方那些屏息凝神的臣子,心中却出奇地没有快意。反而有一种莫名的烦躁和复杂。
我真的要废了他吗?废了他,然后呢?立二皇子?他勇武有余,谋略不足。立三皇子?
他聪慧,却心机过深。我的目光,不由自主地又飘向了东宫的方向。消息很快传到了东宫。
我特意派了心腹太监去“探望”,实则是观察他的反应。太监回来后,一脸的困惑。他说,
太子殿下听闻废储的消息后,脸上没有任何表情,没有惊慌,没有愤怒,甚至没有一丝波澜。
他只是淡淡地“嗯”了一声,然后继续低着头,用一块软布,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一块玉佩。
“那是什么玉佩?”我下意识地问。“回陛下,奴才瞧着,
像是……像是已故元后娘娘的遗物。”我的心,又被什么东西不轻不重地刺了一下。
他竟然平静至此?他是真的不在乎,还是已经绝望到麻木了?或者,他是在用这种方式,
向我示威?那一夜,我罕见地失眠了。我在甘露殿的书房里枯坐到深夜,鬼使神差地,
我打开了一个尘封多年的紫檀木箱。箱子一打开,一股陈旧的木香扑面而来。里面放着的,
都是些孩子们幼时的玩意儿。
我一眼就看到了那个东西——一只用木头雕刻的、形态笨拙粗糙的小老虎。
这是李昭六岁生辰时,送给我的寿礼。我记得那天,他献宝似的捧着这只小老虎,
小脸上满是骄傲。他说:“父皇属虎,恒儿刻一只大老虎送给父皇,保护父皇!
”他的小手因为刻这只老虎,被木刺扎了好几个口子,却一点也不觉得疼。
我拿起那只木老虎,粗糙的边缘硌着我的手心。那时的父子情深,那时的温情脉脉,
仿佛就在昨天。我的心,不可抑制地动摇了。他是我和元后唯一的孩子。
我真的要为了那点可笑的帝王颜面,废掉他吗?我真的要让元后在九泉之下,都不得安宁吗?
我拿着那只木老虎,在殿内站了许久许久。夜风从窗外吹进来,带着一丝凉意。最终,
我还是将那只木老虎,重新放回了箱底。“咔哒”一声,铜锁落下。我将那份动摇,
连同那段温情的回忆,一同锁进了箱底。我是皇帝,帝王不能有感情的羁绊。废储之事,
关乎江山社稷的未来,岂能因一点匹夫之仁而动摇?我告诉自己,我的犹豫,
只是因为时机未到。我需要一个更充分的理由,一个让他永无翻身之地的理由。
我没有当场决断,不是因为心软,而是因为,我要等。等一个能让我名正言顺地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