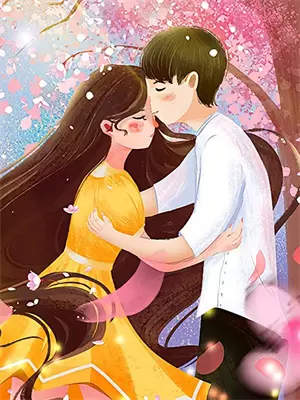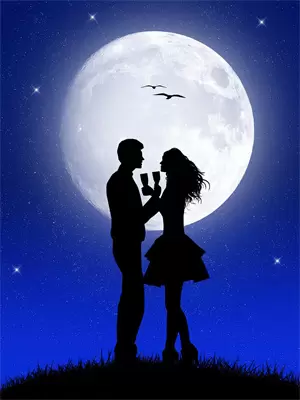我是被一阵剧烈的眩晕拽进1937年的。那天下午,图书馆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,
我趴在满是灰尘的旧书堆里,指尖刚触到一本烫金剥落的日记,
太阳穴就像被钝器狠狠砸了一下。眼前的铅字突然扭曲成旋涡,
耳边的空调声变成刺啦刺啦的电流音——再睁眼时,鼻腔里灌满的是油墨混着煤烟的味道,
视线里是褪色的蓝布窗帘,窗台上摆着一盆半枯的文竹。“文秀,过来。
”柜台后传来温和的声音,我顺着那声音看去,一个戴圆框眼镜的中年男人正踮着脚,
把一叠泛黄的传单塞进《论语》的封皮里。他手指修长,指甲缝里嵌着墨渍,
袖口磨出了毛边,却洗得干干净净。这是苏文秀的父亲,苏明远,
保定城里小有名气的读书人,开着这家“文兴书局”,专卖些新旧书籍。
我知道他会在三天后死在日军的刺刀下。作为2023年的大专生林薇,
我此刻像个偷藏在罐子里的影子,被硬生生塞进了1937年的苏文秀体内。
我能感受到她棉布旗袍下温热的皮肤,能听见她胸腔里平稳的心跳,
甚至能尝到她刚喝进嘴里的那口菊花茶——微苦,带着点回甘。可我发不出任何声音,
动不了任何一根手指,只能透过这双十七岁的眼睛,眼睁睁看着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
苏文秀走过去,帮父亲把那本夹了传单的《论语》放回书架最高层。“爹,
这些东西......”她声音很轻,带着少女特有的怯懦,
“要是被查到......”“查?”苏明远推了推眼镜,镜片后的眼睛亮得很,
“他们能禁了书,还能禁了人心?”他从怀里掏出块牛皮糖,剥开纸塞进女儿手里,“拿着,
给文月的。”文月是苏文秀的妹妹,才十岁,正趴在里屋的八仙桌上描红。
我看见她梳着两条麻花辫,发梢系着红绸子,笔尖在宣纸上歪歪扭扭地写“人之初”。
阳光透过窗棂,在她脸上投下格子状的光斑,她鼻尖上沾了点墨,像只偷喝了墨汁的小猫。
三天后的那个清晨,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。苏文秀住在里屋,此刻正抱着文月缩在床角。
我能感受到她的心跳快得像要蹦出来,文月的指甲深深掐进她的胳膊,疼得她倒抽冷气。
砸门声越来越响,混着日军的嘶吼和枪托撞门的闷响,门板上的漆皮一块块剥落,
露出底下泛黄的木头。“爹!”苏文秀突然想起什么,要往外冲,却被苏明远死死按住。
他把她们往床底推,自己转身从书架上抽出那本夹着传单的《论语》,
想往灶膛里塞——可已经来不及了。日军踹开大门时,苏文秀正从床缝里往外看。
我看见刺刀的寒光扫过书架,扫过父亲的眼镜,扫过文月掉在地上的红绸子。
一个戴钢盔的士兵一把揪住苏明远的衣领,另一个翻出了那本《论语》,
传单从书页里散落出来,像一群白色的蝴蝶。“八路的干活!”日军吼着,
皮带“啪”地抽在苏明远脸上。眼镜掉在地上,镜片碎成了蛛网。他没躲,
只是盯着那些士兵,一字一句地说:“那是孔圣人的书,你们也敢动?
”第二下皮带抽在他胸口,第三下落在他背上。苏文秀在床底死死咬住嘴唇,
血腥味在嘴里弥漫开来。我想让她别咬,想让她闭上眼,可她的睫毛像被钉住了,
死死盯着父亲蜷缩的背影。刺刀捅进去的那一刻,没有想象中的巨响。只有一声闷哼,
像是什么重物掉进了水里。苏明远倒下去时,手指还在抽搐,似乎想抓住什么。
阳光照在他染血的白衬衫上,那片红像朵迅速绽开的花。文月尖叫起来,
苏文秀猛地捂住她的嘴,自己的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,砸在床板上,嗒嗒作响。
日军开始放火,书架燃起来的味道很呛,是纸张燃烧的焦糊味,混着父亲的血腥味,
成了我和苏文秀共同的噩梦。直到天黑透了,她们才从床底爬出来。
文兴书局已经变成了黑黢黢的架子,苏明远的尸体被烧得蜷曲,
只能从那只没烧完的布鞋认出是他。苏文秀没哭,只是跪在地上,
用手一点点把那些没烧透的书页拢起来,指尖被烫出了水泡也没察觉。“姐,
爹还能活过来吗?”文月拉着她的衣角,声音抖得像风中的叶子。苏文秀把妹妹搂进怀里,
下巴抵着她的发顶。我能感受到她喉咙里的哽咽,像有块石头堵着。“能,”她终于开口,
声音哑得不像她的,“等咱们打跑了鬼子,爹就回来了。”那天晚上,
她们揣着父亲藏在床板下的几块银元,离开了保定城。苏文秀穿着父亲留下的蓝布褂子,
太长了,袖口卷了三圈,怀里抱着文月,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月光下的土路上。
我知道她们要去哪里——历史的洪流会把她们推向热河山区,推向那些等着她们的人。
二逃亡的路走了二十七天。苏文秀把银元缝在文月的鞋底,夜里就睡在破庙或草垛里。
文月开始咳嗽,小脸烧得通红,苏文秀背着她走,后背的衣服被汗水浸得发潮,又被风吹干,
结出一层白花花的盐渍。路过一个村子时,她们讨到了半碗稀粥。文月小口喝着,
苏文秀看着她,自己那碗却动也没动。我知道她饿——胃里空得发慌,像有只手在里面拧。
可当文月把勺子递到她嘴边时,她还是摇了摇头:“姐不饿。”第八天,文月烧得迷迷糊糊,
嘴里直喊“爹”。苏文秀抱着她坐在路边哭,眼泪滴在文月滚烫的脸上。我看见她的绝望,
像掉进了冰窟窿,连骨头缝里都透着冷。就在这时,一个穿灰布军装的年轻人走了过来,
背着把步枪,帽檐下的眼睛很亮。“同志,需要帮忙吗?”他问,声音很温和。
苏文秀猛地站起来,把文月护在身后,警惕地看着他。我知道这是地下党的人,
是来接她们的,可苏文秀不知道。她经历的恐惧太多了,已经不敢相信任何人。
年轻人没再靠近,只是从背包里掏出个小布包:“这是退烧药,给孩子用上吧。
前面有我们的联络点,能让孩子睡个安稳觉。”他把布包放在地上,后退几步,
“我们是打鬼子的,信得过就跟我走。苏文秀看着地上的药包,
又看了看怀里烧得发抖的文月,最终还是捡了起来。联络点藏在一个山坳里的破庙里。
里面已经有十几个人,大多是妇女和孩子,还有几个穿军装的人在擦枪。
一个剪着短发的女人走过来,接过文月,熟练地给她喂了药,又找了块干净的布巾沾了凉水,
敷在她额头上。“我叫陈兰,是这里的负责人。”女人笑着说,眼角有几道细纹,
“你爹的事,我们听说了。他是个好同志。”苏文秀的眼泪又涌了上来。这些天来,
她第一次听到有人提起父亲,不是用“八路”或“反贼”,而是“好同志”。
“我想加入你们。”她说,声音不大,却很坚定,“我爹能做的事,我也能做。
”陈兰看着她,看了很久,点了点头:“交通员,敢做吗?要走夜路,要过封锁线,
随时可能......”“我不怕。”苏文秀打断她,指尖攥得发白,“只要能打鬼子,
我什么都敢。”那天晚上,文月终于退了烧,睡得很沉。苏文秀坐在火堆旁,
听陈兰讲那些关于“抗日”“解放”的词。我知道这些词背后的重量,
知道它们会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,可苏文秀只是安静地听着,眼里的光一点点亮起来,
像被风吹燃的火星。她的第一个任务,是送一份情报到三十里外的赵家峪。
陈兰给了她一个绣着月季花的荷包,说情报藏在夹层里,接头人是个卖糖葫芦的老头,
暗号是“甜吗?”“酸掉牙了”。出发前,苏文秀对着破庙的镜子梳了梳头发。
镜子是块碎镜片,照出她苍白的脸和眼下的青黑。她把父亲留下的钢笔别在衣襟上,
又摸了摸文月熟睡的脸蛋,深吸一口气,走进了夜色里。我跟着她走在田埂上,
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。路过一片坟地时,她吓得打了个哆嗦,脚步却没停。
我知道这条路是安全的,可她不知道。每走一步,她的心跳都在加速,
手心的汗把荷包浸得发潮。快到赵家峪时,突然传来狗叫声。苏文秀赶紧钻进路边的高粱地,
趴在地里不敢动。我看见三个伪军举着火把走过来,皮靴踩在泥地里的声音离得很近,
烟草味顺着风飘过来,呛得她直咳嗽。“他娘的,这鬼天气。”一个伪军骂着,
“听说城里又抓了几个八路,全给毙了。”另一个笑起来:“毙了好,
省得老子天天熬夜巡逻。”他们的声音渐渐远了,苏文秀才敢爬起来。
高粱叶割破了她的胳膊,渗出血珠,她却像没感觉似的,只是抓紧荷包,跑得更快了。
在赵家峪的村口,她果然看见个卖糖葫芦的老头。红灯笼在风里晃,糖衣裹着的山楂透着亮。
“甜吗?”苏文秀走上前,声音有点抖。老头抬起头,
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:“酸掉牙了。”情报交出去的那一刻,苏文秀的腿一软,
差点坐在地上。老头给了她一串糖葫芦:“拿着,路上吃。”她没舍得吃,用干净的纸包好,
想带给文月。往回走时,天已经蒙蒙亮了,田埂上有早起的农人在耕地。
苏文秀看着他们扶着犁,吆喝着牛,突然觉得这平凡的早晨真好。
她想起父亲说过的“国泰民安”,原来就是这样的——有地种,有饭吃,
不用担心明天会不会被鬼子杀死。回到联络点时,文月还在睡。苏文秀把糖葫芦放在她枕边,
自己坐在火堆旁,啃着陈兰递来的窝头。窝头很干,剌得嗓子疼,可她吃得很香。
我知道这只是开始,更难的路还在后面,但此刻,她眼里的光,比火堆还要亮。
三我跟着苏文秀的脚步,在冀热大地的沟壑与山岭间穿行,
认识了那些在历史缝隙里挣扎的人。赵老栓是在热河的林海雪原里遇见的。
那是1938年的冬天,雪下得齐膝深,苏文秀去送一份关于日军“扫荡”计划的情报,
走到半路迷了路。就在她冻得快要失去知觉时,一个穿着兽皮袄的老头背着柴捆,
从林子里钻了出来。“丫头,你咋在这儿?”老头的声音像被冻住了,结着冰碴子。
他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,眼角堆着两坨高原红,手里拄着根磨得发亮的木杖。
苏文秀冻得说不出话,只能指了指怀里的情报。老头没再多问,把她架到背上,
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林子里走。我能感受到他后背的温暖,隔着厚厚的兽皮,像个小小的火炉。
他家在山坳里的一间小木屋,墙上挂着猎枪和几张兽皮。老太太早没了,
儿子在县里当小学老师,去年日军“扫荡”时没跑出来,被活活烧死在教室里。
老头说起这些时,正用粗糙的手给苏文秀搓着冻僵的脚,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。
“这林子,我闭着眼都能走。”他往灶膛里添了块柴,火苗“腾”地窜起来,
“鬼子想来搜山?哼,让他们来,来了就别想回去。”第二天,老头带着苏文秀走山路。
他踩在雪地上悄无声息,像只山猫,总能在最隐蔽的地方找到路。路过一片松林时,
他突然停下来,指着雪地上的脚印:“看,这是鬼子的军靴印,昨晚刚过的。
”又指着另一个浅点的脚印,“这是咱们的人,估计是受伤了,走得慢。”苏文秀看着他,
突然明白了陈兰说的“群众是水,我们是鱼”。这些土生土长的山民,
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。后来赵老栓成了游击队的向导,带着队员们在林子里打伏击。
有一次,日军来了一个中队,把他们围在一个山坳里。
赵老栓带着大家从一条只有兔子能钻的石缝里逃了出来,自己却为了引开日军,
往相反的方向跑。“你们先走!我这把老骨头,怕他们个球!”他吼着,
举起猎枪朝日军放了一枪。我看见他被日军围在雪地里,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根木杖。
子弹打穿他的胸膛时,他没倒下,只是看着队员们逃走的方向,笑了笑。雪落在他脸上,
很快就被血染红了。苏文秀在石缝里看着这一切,牙齿咬得咯咯响。我知道她心里的恨,
像被点燃的汽油,烧得五脏六腑都疼。可她不能出去,她怀里还有情报,
还有比仇恨更重要的东西。马德胜是在一次接头时认识的。他原是东北军的骑兵,
热河沦陷后部队打散了,带着几个弟兄在山里打游击,算是个“草莽英雄”。
第一次见苏文秀,他正蹲在石头上啃烧鸡,油乎乎的手往裤子上擦。“陈兰那娘们,
咋派个丫头片子来?”他斜着眼看苏文秀,嘴里嚼得啧啧响,“这可是玩命的活儿,你行吗?
”苏文秀没理他,把情报递过去。他接过来,用牙咬开蜡封,看完后往怀里一塞,
突然笑了:“行啊丫头,胆儿不小。跟我说说,城里的鬼子最近有啥新鲜事?
”他其实是个面冷心热的人。知道苏文秀带着文月,
总时不时让人送些吃的来——有时是半只野兔,有时是几块红糖。有一次,
苏文秀送情报时遇到伪军盘查,是他带着弟兄们从林子里打了几枪,把伪军引开了。“丫头,
以后遇到事就喊‘马德胜’,老子这名号,在这一带还好使。”他拍着胸脯说,